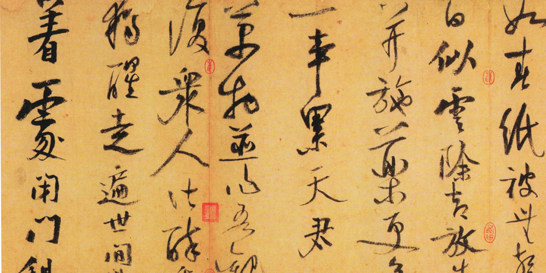一
不论在大众传播空间里,还是在学术语境中,“爱国诗人”都是陆游身上的不二标识。在“中国知网”输入“陆游”、“爱国”两个关键词,相关论文就有五十多篇。陆游的爱国诗人形象,不仅在国内广泛为人接受,而且早在1946年就通过克拉拉·凯德琳·扬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中国的爱国诗人——陆游的剑诗》)一书传播到了国外。
但问题在于,陆游的九千多首诗中,爱国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并不靠它打动同时代直到清末的读者。钱锺书曾概括过陆游诗歌的两类主题:“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同时,钱锺书补充说:“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宋诗选注·序》)的确,陆游同时代人中鲜有人对他的爱国诗作过高度评价,遑论将这些视为他诗歌的主要成就。杨万里说:“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千岩摘稿序》)“敷腴”本为喜悦貌,杨万里好以己意用之,与枯槁相对,是充盈丰满的意思。朱熹说:“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如此篇者,初不见其着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答徐载叔》)朱熹说的“此篇”指 《寄题徐载叔秀才东庄》,“读之爽然”、“有诗人风致”、“语意超然”,显然不是慷慨悲愤的爱国诗。陆游爱国主题的诗歌亦很少能入明清两代的选本。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共选陆游诗105首,能勉强算得上爱国诗的只有《短歌行》《登诸葛武侯书台》《忆昔》等寥寥五首。吴之振等编选的《宋诗钞》尽管推崇陆游“爱君忧国之忱”,可在约710首诗当中,仅选了《寄陈鲁山》《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黄州》等36首爱国诗,所占比例仅为二十分之一。直至陈衍《宋诗精华录》选陆游诗共47首,几乎全为后一类主题的诗歌,为人熟知的《书愤》《十一月风雨大作》《夜泊水村》《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等爱国诗名篇无一入选。
二
清末以来,陆游的形象有一个重大的转换,原本占主导的闲适细腻被忽略不提,而历来受忽视的悲愤激昂则逐渐占据各类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字及诗歌选本的空间。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四首中的前二首发表于1902年5月22日 《新民丛报》第8号,其一云:“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其二云:“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此二诗经常被人引用,几成评价陆游的定论。然而细读二诗就会发现梁氏的看法很成问题,首先,“集中什九从军乐”与《剑南诗稿》的实际收诗情况不一致。其次,“辜负胸中十万兵”与陆游的实际军事才能差距很大。放翁好言战事,而同时代人却从来不提他有什么军事长才。第三,“百无聊赖以诗鸣”也与陆游的生活不符,他很少“百无聊赖”,晚年蛰居山阴还依然谋求做提举宫观的领祠,以致杨万里嘲讽他是“更羡夔龙集凤池”(《寄陆务观》)。
梁启超淹通古今,如果说他的误解陆游是由于知识盲点,自然无法让人满意;如果说这是他未经深思的兴发之言,却更让人无法理解,因为在他后面紧接着的是“五四”文人一系列的应和声音,犹如山谷里洪大的回响,震荡过整个二十世纪。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就以陆游的《夜泊水村》警醒青年要为新建之“共和国”争自由。闻一多在1922年给梁实秋一封未寄出的信中极为赞赏陆游的“襟怀开旷,操守正大,自信不移”。郑振铎的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评价他“意气豪迈”、“灏漫热烈的爱国之呼号,常见于他的词与诗里”。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则说他“所作诗词多慷慨悲壮”,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未已,时时从作品里流露出来”。这两部颇具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对于陆游诗歌“闲适细腻”的风格竟无一字提及。更有趣的是,陆游在中国诗史中的地位有时甚至还超过杜甫:“杜诗虽兼具爱国之忱,然只有悲无壮,苍凉有余,雄快不足,千余年来,悲壮雄快并具者,其惟陆放翁乎?”(堃垕《爱国诗人——陆放翁》)
从诗选看,陆游“悲壮雄快并具”的诗所占比重飙升,与明清选本适足形成对照。陈幼璞1937年出版的《宋诗选》以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各体分选宋代诗家,不但爱国类主题的悲愤激昂已经完全占据陆游诗风的主导,并且除五绝外,所选各体数量均超过包括苏轼、黄庭坚在内的任何一位宋代诗人。程千帆、缪琨在1957年出版的《宋诗选》中,共选陆游诗歌17首,只有《沈园》二首与《剑门道中遇微雨》不算爱国诗。陆游的诗歌专集也同样如此,在朱东润、游国恩、陆应南各自选注的《陆游诗选》中,前一类主题的比重均占绝对优势。因抗战形势的需要,许文奇在1933年还专门选注了《放翁国难诗选》,所选诗篇自然更“以发抒国难愤激敌寇者为限”。
由此可见,从梁启超诱导到陈独秀、朱东润等人构建完成的陆游“爱国诗人”形象,既非盲目,亦非无意,而是在“共同体意识”主导下有目的有系统的工程,这就不能不提“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了。梁启超发表《读陆放翁集》的这一年,也正是他写成 《新民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之时。在此二文中除了表达中国自古无“爱国精神”、“国家观念”的感叹外,梁启超非常坚定说:“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目睹了英法德美意诸国的崛起,梁启超确信中国只有发展出欧美列强式的民族主义才不至于像波兰印度越南朝鲜相继亡国。但是起源于欧美的民族主义枝芽能否在中国嫁接成功需要有相对应的茎根,方可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植株。陆游与他所处的宋代,确乎最适合充当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赖以成长的历史基础。梁启超认为古代中国的“天下意识”削弱了“民族意识”,所以诗歌中往往突出反战的主题,而到了陆游这里完全改观:“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慕为国殇,至老不衰。”(《读陆放翁集》其一之小注)闻一多则认为宋以前中国的主导思潮是“家族主义”,到了宋代才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他庆幸地说道:“历史进行了三分二的年代,到了宋朝,民族主义才开始发芽。”(《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不论是“天下意识”,还是“家族主义”,在解决现实危机上,都无法与“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而陆游正是这一思想萌芽时期最有代表的诗人。
三
在举世一致将陆游定性为爱国诗人的历史大潮中,却有两位思想者洞察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深刻见解。
第一个是鲁迅。他在1933年写的《豪语的折扣》 中批评这位乡贤的空言爱国:“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鲁迅已经预感到,诗歌文本中悲愤激昂的“豪语”,不但与实践中的爱国行为并不等价,更会给文学带来极大的负面性。鲁迅一向不认为文学应当作为革命的武器,他把文学摆在对革命的“无用”位置,其实也就意味着将文学从革命中独立出来而保持自由的品格。
第二个就是钱锺书。他在1946年写的一则英文书评中说:“现代中国往往将古代的历史事件与现实困境相比较,陆游这些慷慨激昂的诗篇吻合了今天爱国青年的需求。……部分中国文学的大学教授发现了一种通过抒写爱国者来表达爱国情感的方式,于是陆游的诗便成为他们写文章的‘文本’或‘前文本’。”钱氏指出了陆游悲愤慷慨的诗歌为何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文本载体。他的《谈艺录》评论陆游诗的篇章迥异于时流,认为陆游与白居易、贾岛、温庭筠等中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并提出:“放翁高明之性,不耐沉潜,故作诗工于写景叙事。”这正是对将陆游诗歌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主流思潮之重要反拨。
当然,回过头来说,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陆游成为构建清末以来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符号,是他的大幸。陆游或许怎么也想不到,那些一直未被看重的爱国诗会在八百年后受到人们如此的推崇,乃至催化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对于诗本身来说,狭隘地以民族主义解读陆游未尝不是他的不幸。赵翼曾总结:初期的工巧、中期的宏肆、晚期的平淡,堪称陆游诗风之“三变”。又指出:使事、写怀、写景,可见出陆游诗的“功力之精”(《瓯北诗话》卷六)。这些特点虽然代表了明清两代接受陆游诗的主要方面,却并没有在现代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及诗选上有过多提及,更不用说他原本也可以像屈原、杜甫、李商隐、周邦彦、姜夔那样在新诗艺术层面发生正面影响。负荷了清末以来文人的国族想象是陆游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悲愤激昂的爱国诗却未必能奠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钱锺书所说:“诗歌是恨不能吞火的爱国者最后的避难地。纸上的英雄诗体与纸上的英雄相等价,这在现代文人的写作中非常普遍,不值得特别予以嘉许。”这句“诗歌是恨不能吞火的爱国者最后的避难地”,背后其实隐含了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更为严厉的指斥:“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厘清陆游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纠葛,让思想的归思想史,让文学的归文学史,可以让我们从不同层面了解中国古代诗人丰富而辽阔的精神世界。
(下载iPhone或Android应用“经理人分享”,一个只为职业精英人群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的分享平台。不做单纯的资讯推送,致力于成为你的私人智库。)
作者:潘建伟
来源:中国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