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搜词
12bet-“素贞环蛇”发现者:专业找蛇17年,曾多次被蛇咬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消息,成都南一环边外,走进一栋上世纪末建成的楼,就跨入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办公室。这里的一切充满年代感,水泥石阶磨得锃亮,白色木门上的门牌号颜色斑驳。
“有蛇出没,请注意!”
一个房间的门上贴着一张A4纸,推门进去,房间分成两半,一半,存放着活体蛇样本,另一半,是丁利的办公室。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利,最近成了媒体“围攻”的对象。算上红星新闻记者,这已是他当天接受的第三家媒体采访。但他脸上并无不耐烦之意。说到尽兴处,还会用双手比划,声音也高昂了起来。
这一切,要推到采访前一天。
24日晚,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发文称:近日,一支以中国学者为主的研究团队在国际著名分类学期刊Zookeys上发表对我国银环蛇物种进行厘定的文章,并描述了一种以前未被发现的剧毒蛇——素贞环蛇Bungarus suzhenae Chen, Shi, Vogel, Ding, Shi, 2021。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环蛇属物种进行命名,并使用“素贞环蛇”来命名该物种。该名字源于《白蛇传》中广为人知的神话人物白素贞。
因以“素贞”为名,这个最早发现于缅甸、后在云南盈江被确认身份的新物种迅速“破圈”,冲上微博热搜。
丁利是素贞环蛇研究团队负责人,这是他乐于见到的场景,“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科普。我们希望更多人认识它,了解它。”说完,他笑了笑。
3月25日下午,在成都生物所一方狭小的天地内,52岁的丁利给记者讲起过去17年来的故事。那是科学家与蛇的故事,也是一段关于冒险的故事。
还原素贞环蛇发现全过程:
曾造成一死一伤,并非首次以神话人物命名
在丁利的叙述中,素贞环蛇的发现,离不开两个人:美国加州科学院两栖爬行动物学家Joseph Slowinski,成都的两爬爱好者侯勉。后者本职工作是一名大学行政工作人员。
2015年夏天,侯勉独自一人到云南盈江进行野外考察。丁利曾告诉他,双全白环蛇是此处的地模标本。当时,侯勉误将一条“素贞环蛇”幼蛇认做双全白环蛇,“一激动就下手去抓,抓了就被咬了。”
幸运的是,随行有一司机,将其送往邻近县上医院,历经70多个小时抢救才得以脱险。
后来,据侯勉回忆,盈江的这种“银环蛇”咬伤后局部疼痛明显,并伴有伤口周围皮肤发黑,与被银环蛇咬伤局部无明显痛感、不红不肿等临床表现不同。也是在这时,丁利才开始注意到,盈江的环蛇与已知的银环蛇可能不是一个物种。
如果沿着历史的脉络回溯,会发现,类似的事件早有发生。
2001年,Joseph Slowinski在缅甸野外考察中,不慎被标记为白环蛇属的幼蛇咬伤,因医疗救援无法及时赶到,后不幸身亡。
两相关联,丁利判断,这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2016年伏季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风雨欲来。丁利一行人再次来到云南盈江,由侯勉带路,前往一年前的事发地点,寻找素贞环蛇。
丁利记得那一晚的所有细节:独自一人驱车的他在马路上意外发现一条素贞环蛇,刚下车准备去抓,天上就下起瓢泼大雨。
他一手提着蛇尾巴,一手去后备箱里找装袋。除了大雨,他还要时刻提防着手里的小蛇,淬满毒素的毒牙随时可能来上一口。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近20分钟,当把蛇顺利放进容器里时,他浑身已被大雨淋透。
遗憾的是,由于只有一个人,腾不出手,未留下珍贵的视频资料。
“素贞”一名的由来,也颇有渊源。
在生物学领域,给物种命名,采取的是双命名法,即一个物种名的单词加一个属名。“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是其命名原则之一。到后期,如果发现其他物种也有类似特征或特征复杂不易用一个词准确表达时,就可以用首次发现地名或地理分布区范围等。这之外,人名,也是命名的方法。
对于素贞环蛇来说,既找不到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用地名亦不合适(在缅甸、云南均有发现),最适合命名的侯勉和Joseph Slowinski又均已有命名物种,“这个物种和人的关系密切,关乎人的生命安全,为了让大家都记住它,我们采用了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素贞’。”
实际上,用神话人物为新物种命名,并不是首次。比如,此前,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研究团队曾在四川发现一种有轻微毒性的颈槽蛇,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螭吻颈槽蛇。
螭吻,传说乃龙第九子,擅火。该颈槽蛇喜欢吃萤火虫,会将萤火虫体内毒素积攒到自身体内以防御天敌。萤火虫的英文名是firefly,因此就有了这个名字。
除了素贞环蛇,近年来,成都生物所也在密集地发现新物种。“这源于多年来的积累。”丁利说,发现一个新物种并非一蹴而就,前期需要做大量工作,不仅要进行复杂的比较,还要接受同行评议,最终才能公诸于世。
科学家与蛇的故事:
多次被蛇咬伤,但最危险的不是蛇
在近2个小时的采访中,不时有电话进来。接电话时,丁利的左手总会微微颤抖。
他将左右手食指伸出并拢,问记者,“你看,是不是左边手指要细一些?”
这是2009年他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不慎被蛇咬到后留下的后遗症,会“微微发麻”。
在17年的科考生涯中,丁利有多次被蛇咬到的经历。但那一次,并不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
时间回溯到2014年7月1日这天,秦岭。
当时,学术界对秦岭蝮蛇的物种分类颇有争议,带着这一课题,丁利捎上一个学生,上了秦岭。
他在马路边一个乱石砌成的石坝前停下,经验告诉他,这里一定有蛇。
石坝大概有200米,丁利第一次走完,一无所获。往回走时,就看到3条蝮蛇趴在那儿,“当时我就非常激动!”
数据当然越多越好。他放弃了捕蛇工具,选择用手抓。为防止抓住的蛇钻回石缝,他一手捏着一条蛇,扔上开阔的马路,准备拍照记录。
其中一条被树枝挡住,掉进了排水沟,丁利赶紧上前用手去抓。钻了一半的蛇被扯出,回头就咬了他一口。
咬伤的部位是左手中指,迅速肿痛。“我有经验,判断这个蛇没那么毒。”于是,他举着肿痛的左手,驱车70余公里回到了住所。
做完处理后,丁利在床上躺着休息了3天。3天时间里,他无法做其他事情,甚至疼得无法入睡。
“但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蛇。”丁利说,气候地质灾害,往往才是最致命的。
有一次,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研究团队要翻过一道陡坡。那是一个笔直的悬崖,往下几十米,就是翻滚的雅鲁藏布江。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需要聘请专业登山队员,前面的人过去后拴上绳子,后面的人再抓着绳子往前走。
但那次出现了意外,前面的人都走了,后面却还剩很多队员。
那个斜坡只有短短约10米,却像一道天堑。
“全是细沙和细石,根本没处下脚。只要脚底稍微一滑,就会掉下悬崖被江水吞没。”当天晚上,只要一闭眼,丁利脑海中翻滚的,就全是这个画面。
还有一次,也是在墨脱。一个晚上,丁利和同伴一前一后走着,突然身后“轰隆”一声。他回头一看,几秒前走过的地方发生山体滑坡,滑落的石头泥土就横亘在丁利和队员中间,他们就这样两两相看,一时无言。
“那你有过动摇,有过害怕吗?”
“动摇倒是没有,后怕是有的。”他说,随着出野外的时候越来越多,胆子会越来越小。“在大自然洪荒的力量面前,人类不值一提。”而遇到这种情况,他会告诉同伴安全第一。
“那你遇到过目标近在咫尺却发生自然灾害无法前往的情况吗?”
“当然有过。我会选择下次再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专注于蛇类分类研究
国内目前只有三五人
“团队?哪儿有什么蛇类研究团队。我们都是大研究团队,涵盖各个研究方向,比如我属于生物多样性中心和生态服务领域的动物行为与仿生学科组。具体的研究大多是一个人,有时候带上一两个学生或合作者,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分工协作。”当记者问起团队背后的故事时,他笑着答。比如素贞蛇的研究,除了丁利,还有两个研究生,也就是本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 ,以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蛇类骨骼研究专家和德国学者,是大家共同协作的结果。
丁利的个人经历,也如他的野外冒险一样,颇具戏剧色彩。
他原是医学出身,当过几年临床医生,因为对蛇类兴趣浓厚,2004年,35岁的他辞职转行,从老家北京千里迢迢来到成都生物所,干起了蛇类研究。“没什么特殊契机,就是喜欢。当时觉得如果这辈子不干这事,我会后悔。”
17年来,每年至少有三四个月在野外,野外考察成了家常便饭。他的一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除了危险,也会遇到很多让他感激的事情。
比如,他记得刚“出道”时,曾花一年多时间,独自一人走遍中国19个省市,采集了127条短尾蝮蛇样本。那时交通很不便利,除了赶绿皮火车,还要坐牛车马车。那一年多时间,他在全国各地受到不同民间爱好者的帮助,有人免费给他当向导,有人帮着他一起找样品。
虽然有情怀的民间爱好者多,但专职于蛇研究的人,却并不多。
丁利告诉记者,与其他两爬类研究不同的是,蛇类研究不仅具有危险性,因蛇行动隐秘,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可能几年都出不了成果。所以专职于蛇类研究的人很少。
少到哪种程度?
在全国最早开展两栖爬行类研究的成都生物所,目前只有丁利一人专注于蛇类分类研究。加上他,国内也只有三五人专注于此。“没有情怀,根本无法坚持。”
“那你会担心后继无人吗?”记者问。
“当然不会。”
事实上,受老一辈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蛇类研究。这些年来,丁利也带过一些学生,最年轻的,才20岁出头。
他指着素贞环蛇申报材料上的一个人名告诉记者,这里的第一作者之一陈泽宁同学,刚来的时候就是个“小白”,既不了解蛇,也很怕蛇。但现在,他在该领域已颇有建树,毕业后也回到其母校任职,未来可能也将从事蛇类研究。
被蛇咬后把毒吸出来有效吗?
有效,但用嘴吸蛇毒可能造成二次中毒
大抵是因为职业关系,聊得尽兴,采访时丁利还做起了科普。
他说,民间有很多治疗蛇伤的方法,但大多都不靠谱。比如用绳子对肢体进行结扎,或是用火烤的小刀划开伤口,这些处理不仅无效,还可能导致并发症。
“尤其不建议绳子结扎。”他说,对于五步蛇、川渝地区最常见的原矛头蝮而言,这种咬伤肢体本身会剧烈肿胀,如果用绳子勒住,很容易造成肢端坏死、溃疡,甚至截肢。“无数病例显示,不用绳子结扎的都没事,只要一用绳子结扎肯定有事。”
对于蛇伤,在业内有一个“黄金三分钟”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咬伤后的三分钟内,如果进行正确的局部处理,将对后期治疗大有助益。而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制造一个负压吸引器,比如小口径的拔火罐,或是用一次性注射器,切掉注射器一端,用切口整齐的一面对着伤口,将蛇毒吸出后,用酒精破坏蛇毒。
如若实在找不到吸引器,也可以尝试用嘴吸出蛇毒,“但该法可能随着口腔疾病造成二次中毒。”所以对公众而言,蛇伤后最有效的办法是尽早送到有治疗蛇伤经验的正规医院进行诊治。
“您长期与家人分隔两地,也长期在野外,是否觉得这份工作很清苦?”采访结尾,记者问。
“丰富多彩的蛇类王国,会让我忘记一切烦恼。”他笑着说,这份工作的意义,已远超过了个人爱好。
“物种分类是人类认知地球生命的基础,也是生物学大厦的基石,如果没人做这件事,大厦可能会‘倾覆’。”蛇类研究与人类密切相关,蛇毒毒理、蛇伤流行病学、蛇伤临床防治等学科也离不开它。“一个新物种的发现,也会为蛇伤流行病学和诊疗提供重要参考,意味着可能挽救更多人生命。”
而这,也是丁利所认为的价值所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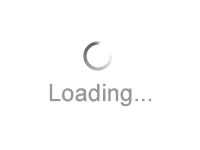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威尼斯官网地址:赞!湖北5人荣登3月“中国好人榜”
威尼斯官网地址:赞!湖北5人荣登3月“中国好人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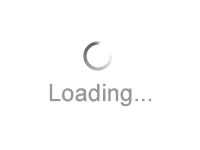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意大利贵宾会是真的吗:乡村“小分队”,发挥基层治理“大作用
意大利贵宾会是真的吗:乡村“小分队”,发挥基层治理“大作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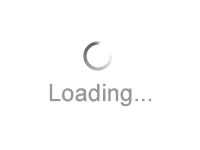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千赢手机app官网:东京奥运圣火在日本长崎用“遣唐使船”传递
千赢手机app官网:东京奥运圣火在日本长崎用“遣唐使船”传递
-
 12bet备用网址网页版:多地延长紧急状态 日本首相回应“奥运还能
12bet备用网址网页版:多地延长紧急状态 日本首相回应“奥运还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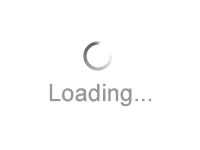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beat365官网地址是多少:贡献“她力量”撑起“半边天” 涪陵区妇
beat365官网地址是多少:贡献“她力量”撑起“半边天” 涪陵区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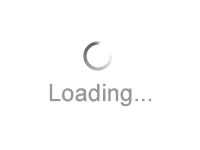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mg官方网站:武汉4月“三站一场”文明程度排名揭晓
mg官方网站:武汉4月“三站一场”文明程度排名揭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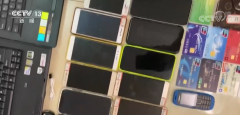 威尼斯人下载app:“跑分”“菜商”“水房” 电信诈骗黑话大揭
威尼斯人下载app:“跑分”“菜商”“水房” 电信诈骗黑话大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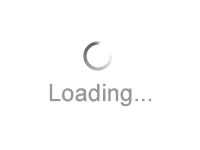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永利澳门娱乐场app:电梯“吃人”事件频发,有多少电梯超龄服役
永利澳门娱乐场app:电梯“吃人”事件频发,有多少电梯超龄服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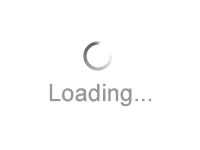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亚博app下载安卓版:昌平区回龙观街道回龙观新村社区探索实行“
亚博app下载安卓版:昌平区回龙观街道回龙观新村社区探索实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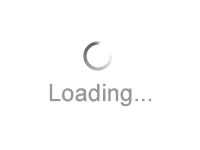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凯发ag旗舰厅:近400岁的沈阳故宫越“活”越年轻
凯发ag旗舰厅:近400岁的沈阳故宫越“活”越年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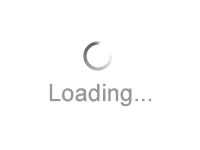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韩国瑜复出布局 名嘴陈挥文:要想通3件事02-19
韩国瑜复出布局 名嘴陈挥文:要想通3件事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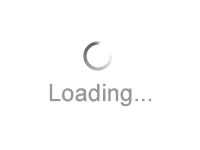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1欧元甩卖王室城堡给政府,德国汉诺威王子被父亲起诉02-19
1欧元甩卖王室城堡给政府,德国汉诺威王子被父亲起诉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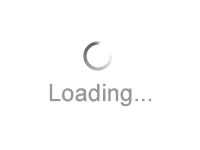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因疫情连失亲人打击不断 美国民众欲哭无泪02-19
因疫情连失亲人打击不断 美国民众欲哭无泪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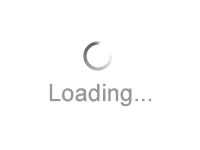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美国前女主播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官方未公布死因02-19
美国前女主播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官方未公布死因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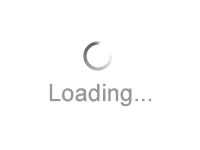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男子抓拍举报占用应急车道18起!交警:已全部录入02-19
男子抓拍举报占用应急车道18起!交警:已全部录入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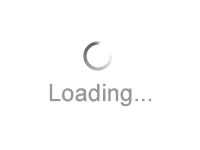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杨幂胸前大深V直播 肩带撑不住北半球露出来了02-19
杨幂胸前大深V直播 肩带撑不住北半球露出来了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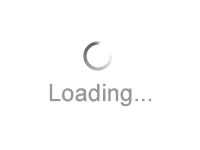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电影票房破亿 女星脱了全裸辣送福利网嗨爆02-19
电影票房破亿 女星脱了全裸辣送福利网嗨爆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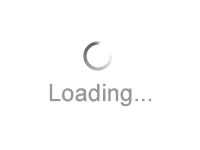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印军高官鼓吹边境对峙“获胜” 分析人士:为莫迪政府“政治减02-19
印军高官鼓吹边境对峙“获胜” 分析人士:为莫迪政府“政治减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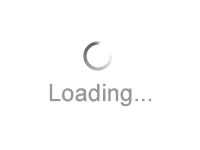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海南离岛免税店春节销售额超15亿元02-19
海南离岛免税店春节销售额超15亿元02-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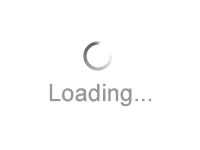 三明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02-19
三明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02-19









